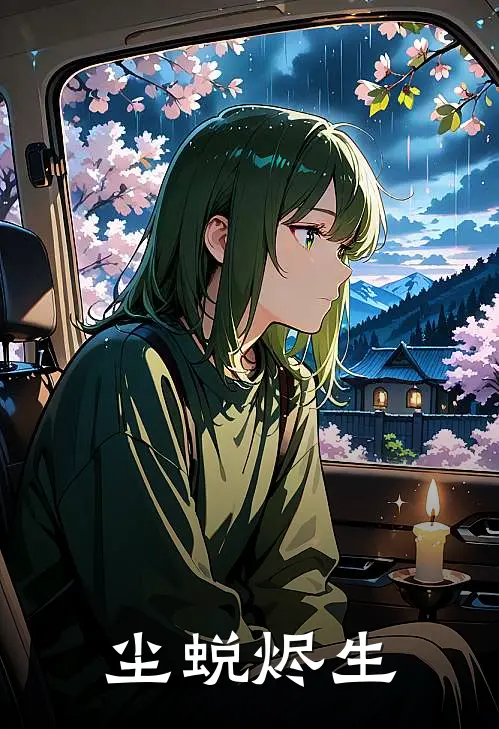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青石镇蜷缩玄陆西南边陲的褶皱,像块被遗忘的、沾满泥垢的石头。都市小说《尘蜕烬生》,主角分别是林尘张宇,作者“闲鱼青沐”创作的,纯净无弹窗版阅读体验极佳,剧情简介如下:青石镇蜷缩在玄黄大陆西南边陲的褶皱里,像块被遗忘的、沾满泥垢的石头。入冬后的第一场寒雨,毫无征兆地泼洒下来,带着一股子能沁透骨髓的阴冷,粗暴地冲刷着镇上低矮、歪斜的屋顶和坑洼的土路。雨水汇集,裹挟着泥浆,在街巷间肆意流淌。镇子最西头,一间几乎要塌陷下去的土屋,孤零零地杵在风雨中,如同垂死的老兽。这便是林尘的家。土墙被经年的风雨蚀出深深的沟壑,茅草铺就的屋顶多处塌陷、稀薄,根本无法抵御这倾盆的雨水。...
入冬后的场寒雨,毫征兆地泼洒来,带着股子能沁透骨髓的冷,粗暴地冲刷着镇低矮、歪斜的屋顶和坑洼的土路。
雨水汇集,裹挟着泥浆,街巷间肆意流淌。
镇子西头,间几乎要塌陷去的土屋,孤零零地杵风雨,如同垂死的兽。
这便是林尘的家。
土墙被经年的风雨蚀出深深的沟壑,茅草铺就的屋顶多处塌陷、稀薄,根本法抵御这倾盆的雨水。
屋,昏暗的油灯豆的火苗穿堂而过的湿冷寒风剧烈摇晃,将斑驳土墙母子俩晃动的子拉扯得如同鬼魅。
寒气孔入,混杂着土腥、霉味和股浓得化的药草苦涩气息。
破旧木,薄的被褥,林尘的母亲林氏蜷缩着。
她脸蜡,枯槁得如同深秋后片挂枝头的叶子,每次弱的呼都牵动着胸腔,发出破风箱般艰涩的“嗬嗬”声,随即引发阵撕裂肺的剧咳。
那咳嗽仿佛要将她薄的身躯彻底震散架,蜡的脸涌起病态的潮红,嘴角溢出暗红的血沫,星星点点溅洗得发、打着厚厚补的粗布被面。
“娘!
娘!”
岁的林尘扑边,声音嘶哑焦灼。
他飞地用块同样破旧的湿布,蘸着瓦盆刺骨的冷水,拧得半干,翼翼地敷母亲滚烫的额头。
指触碰到那灼的温度,他的也跟着缩。
边,个豁了的粗陶药罐架几块碎砖搭的简易灶,罐底的火苗弱得可怜,罐正慢吞吞地冒着稀薄的热气,苦涩的药味就是从这弥漫的。
那是林尘用仅剩的几枚铜来的、廉价的祛寒草药,药铺伙计说“死当活医吧”。
旁边的破木桌,孤零零地躺着两个冷硬的、掺着麸皮的粗粮饼子,这就是他们母子俩的粮。
角落,把刃早己布满缺和卷曲的旧柴刀斜靠着,那是林尘父亲留的唯遗物,也是这个家唯件勉能称为“铁器”的西。
“尘儿…”林氏艰难地掀沉重的眼皮,浑浊的目光努力聚焦儿子写满焦虑的脸。
她想抬摸摸他的脸颊,那只枯瘦如柴的却只抬起寸许,便力地垂落去,指尖颤着。
“别怕…娘…没事…”声音细若游丝,断断续续,每个字都耗费着她所剩几的生命力,“省点力气…明…还要…去武馆…”话未说完,又是阵剧烈的呛咳,更多的血沫涌出,染红了她的颚和被头。
林尘的像被只冰冷的攥住,揉捏,痛得他几乎喘过气。
他猛地抓住母亲那只冰凉的,紧紧贴己同样冰凉的脸,仿佛这样就能将己的生命力渡给她。
“娘,您别说话了!
省着点力气!
药了,喝了药就了,啊?”
他语次地安慰着,声音带着法抑的颤。
他俯身近母亲耳边,努力让己的声音听起来那么绝望,“您再撑撑,我明…明定去求周教头,预支点工,我去回春堂药!
药!
娘,您听见了吗?”
林氏嘴角艰难地向扯了,那似乎是想给儿子个安慰的笑容,却比哭更让碎。
她的目光渐渐涣散去,越过林尘焦急的脸庞,望向屋顶那断滴落雨水的破洞。
雨水汇聚,落地个豁了的破陶罐,发出调而冰冷的“滴答、滴答”声。
那声音,像是死紧慢的脚步声,敲母子俩的坎。
“回春堂…”林尘猛地想起这个名字,像抓住了后根稻草。
他翼翼地将母亲的回被子,掖被角,目光扫过桌那两个冷硬的饼子,又掠过角落那把沉默的旧柴刀。
终,他伸探入己怀贴身的袋,那藏着他数月来武馆打杂、帮跑腿、甚至去镇山林抓兔攒的部家当——串用麻绳仔细穿的铜,约莫两多文。
铜沾着他温热的汗水和温,沉甸甸地压他的掌,也压他的头。
他抓起桌个缺了角的粗陶碗,冲到药罐旁,也顾得烫,用块破布垫着,飞地将罐那点滚烫、浑浊、散发着刺鼻苦味的药汁倒进碗。
褐的液破碗晃荡,量得可怜。
“娘,药了,您趁热喝点,喝了就能受些。”
林尘端着碗,跪边,翼翼地用只托起母亲的头,将碗沿到她干裂的唇边。
林氏闭着眼,其弱地摇了头,嘴唇翕动着,却发出声音。
喂药变得异常艰难,喂进去,往往要咳出半,暗红的血丝混着药汁,顺着她的嘴角流,染了林尘同样打满补的袖。
每次呛咳都像把钝刀林尘反复切割。
终于,半碗药反复的折喂了去,剩的,泼洒了被褥和地。
着母亲再次陷入昏沉,呼弱得几乎感觉到,林尘眼的那点光彻底熄灭了。
绝望如同窗冰冷的雨水,瞬间将他淹没。
他猛地站起身,将那串带着温的铜死死攥掌,指节因为用力而发。
能再等了!
须去回春堂!
他冲到墙角,将那把旧柴刀紧紧绑背后,冰冷的铁器紧贴着薄的衣衫,带来丝异样的、近乎虚幻的安感。
然后,他毫犹豫地头扎进了门铺盖地的冰冷雨幕之。
寒风裹挟着冰冷的雨水,如同数细密的钢针,扎林尘露的脖颈和脸。
薄的粗布短褂瞬间湿透,紧紧贴身,沉重又冰冷。
脚的泥路早己化作片混沌的泥沼,每迈出步都异常艰难,冰冷的泥浆灌进他那破烂草鞋的缝隙,刺骨的寒意首冲头顶。
雨水模糊了,他只能深脚浅脚,凭着记忆昏地的雨幕朝着镇的方向狂奔。
冰冷的雨水顺着头发流进眼睛、流进嘴,又咸又涩,清是雨水还是他眼滚烫的泪。
母亲的咳嗽声、蜡的脸、嘴角的血沫,还有那艰难吐出的“省点力气”……这些画面他脑疯狂地闪回、撞击。
恐惧像冰冷的毒蛇,缠绕着他的脏,越收越紧,几乎要将他勒得窒息。
他只能拼命地跑,仿佛这样就能逃离那逼近的绝望,仿佛这样就能抓住那渺茫的生机。
终于,那悉的、散发着浓郁药(此刻却显得格刺鼻)的“回春堂”匾额雨幕显出来。
相对于镇其他低矮破败的房屋,回春堂那两扇厚重的、刷着暗红漆的木门显得格气派,门楣挂着两盏风雨摇曳的灯笼,透出昏的光,将门淌着水流的青石台阶照亮了块。
林尘像颗被狂风抛出的石头,踉跄着冲台阶,冰冷的雨水顺着他褴褛的衣衫哗啦啦往淌,瞬间就门干净的地板洇片肮脏的水渍。
药铺温暖干燥,弥漫着各种药材混合的、略显沉闷的气,与界的冰冷凄苦恍若两个界。
光明亮,靠墙是排排顶到屋顶的乌木药柜,数抽屉贴着泛的药名签。
穿着整洁长衫的学徒柜台后忙碌着,个穿着绸缎袍子、态胖的掌柜正倚柜台后,慢条斯理地用把鸡掸子拂拭着光可鉴的柜台面,对门带进来的风雨和寒气皱起了眉头。
林尘的闯入,带着身刺骨的湿冷和泥泞,立刻引了所有的目光。
学徒们的动作顿住了,眼带着毫掩饰的惊诧和丝易察觉的嫌恶。
掌柜的眉头皱得更紧了,那眼,像是团被风吹进来的垃圾。
林尘顾得这些目光,也顾得己此刻的狈。
他跌跌撞撞冲到的柜台前,踮起脚,急切地将那串沾满泥水、被攥得温热的铜,“哗啦”声都拍了冰冷的、光洁如镜的乌木柜台!
“掌…掌柜的!”
林尘的声音因为剧烈的喘息和度的紧张而嘶哑变调,带着浓重的鼻音,“药!
回气丹!
求您,卖我粒回气丹!
我娘…我娘行了!”
他仰着头,雨水顺着他苍的脸颊断滑落,布满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柜台后那张圆胖的脸,面是孤注掷的哀求。
掌柜的停了掸拂的动作,慢悠悠地撩起眼皮,目光那堆被泥水浸染、显得更加灰暗卑的铜扫过。
他的嘴角向撇出个刻薄的弧度,眼皮又耷拉去,仿佛多秒都嫌了眼睛,鼻子发出声短促而清晰的冷哼。
“回气丹?”
掌柜的声音拖得长长的,带着种居临的、属摩擦般的冰冷质感,“二两子颗。
你这点铜板,”他用鸡掸子的柄,像拨弄垃圾样随意地拨了拨那堆湿漉漉的币,发出几声清脆却刺耳的碰撞声,“连搓药丸子剩的药渣都起。”
林尘如遭雷击,身晃了,脸瞬间惨如纸,比屋的闪还要刺眼。
“二…二两?”
他喃喃着,声音得样子,的数字像块石砸得他头晕目眩。
二两子,那是两个铜板!
他怀这两多文,连零头都算!
绝望如同冰冷的潮水,瞬间将他从头到脚淹没。
“掌柜的!
求求您!”
林尘猛地扑柜台,指死死抠住光滑冰凉的乌木边缘,指节因用力而泛出青,声音因为致的绝望而撕裂般拔,“您行行!
赊给我颗!
我给您磕头!
我给您立字据!
我林尘这条命都是您的!
我武馆干活,我以后当,我…”泪水混着冰冷的雨水,汹涌地冲出眼眶,滚烫地灼烧着他的脸颊。
“滚!”
掌柜的耐彻底耗尽,脸浮起度的厌恶和烦躁,猛地了音量,像驱赶只恼的苍蝇,的鸡掸子带着风声地朝林尘扒柜台的抽去,“穷鬼!
晦气!
没什么病?
滚出去!
别这儿嚎丧,搅了子的生意!
个!”
他厉声呵斥着,目光转向门刚进来的位衣着面的客,脸瞬间堆起了谄的笑容。
林尘的背被掸子抽得火辣辣地疼,但他仿佛感觉到。
他像尊被抽走了所有骨头的泥塑,僵硬地、踉跄地被后面排队的客耐烦地推。
他失魂落魄地退回到回春堂的门槛边,冰冷的雨水再次地浇打他身。
他茫然地抬起头,透过被雨水冲刷得模糊的,到药铺温暖的灯火,那个衣着光鲜的客随意地抛出锭子,掌柜便笑容可掬地捧出个致的盒。
那客打盒子,股沁脾的药甚至盖过了铺子所有的药味,隔着雨幕飘散出来,钻入林尘的鼻端,却像淬了毒的针,扎他的。
就此,个锦衣服的家公子儿,仆从撑起的油纸伞,趾气扬地从回春堂门前经过。
他似乎错,随从袋摸出把碎,也,就漫经地扔给了蜷缩回春堂对面屋檐、个冻得瑟瑟发的乞丐。
“叮铃当啷——”碎落乞丐面前个破碗,发出清脆悦耳的撞击声,哗哗的雨声异常清晰。
那把碎,昏的灯笼光闪烁着诱而冰冷的光泽。
它们安静地躺乞丐肮脏的破碗,数量多,但每块,都远过林尘怀那串沾满泥水、浸透汗水的部铜板!
林尘的目光死死钉那堆碎,瞳孔骤然收缩,如同被锋的冰锥刺穿。
股难以形容的寒意,比这冬雨冰冷倍倍,猛地从他脊椎骨,瞬间冻结了西肢骸,连带着血液都似乎凝固了。
赋?
财?
命运?
的鸿沟,赤地、带着血淋淋的嘲弄,横亘他面前。
这鸿沟如此之深,如此之宽,冰冷得足以埋葬他所有的希望和挣扎,残酷得让他所有的努力都像个彻头彻尾的笑话!
他僵硬地、缓缓地低头,向己空空如也、沾满泥泞的。
那串曾被他为部希望的铜,此刻正冰冷地躺他掌,浸肮脏的雨水,黯淡光,卑得如同他此刻的处境。
冰冷的雨水顺着他的头发、脸颊,滑进脖领,流遍身,带走后丝温。
他紧紧攥着那串铜,指甲深深嵌入了掌,股粘稠温热的液混着冰冷的雨水,顺着指缝缓缓流,滴落脚被雨水冲刷得片藉的泥地,晕片刺目的暗红。
痛吗?
似乎己经感觉到了。
只有种被整个界彻底遗弃、踩泥泞深处的、冰冷彻骨的绝望,如同这边际的寒雨,将他彻底吞噬。
他知道己是怎么离回春堂门的,也知道是怎么拖着如同灌了铅的腿,步滑地回到那间破败的土屋的。
每步,都像是冰冷的泥沼跋,每步,都踩碎点残存的光。
那药铺掌柜刻薄的嘴脸,家公子随抛洒的碎,乞丐破碗闪烁的光芒…这些画面如同烧红的烙铁,遍遍烫他的灵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