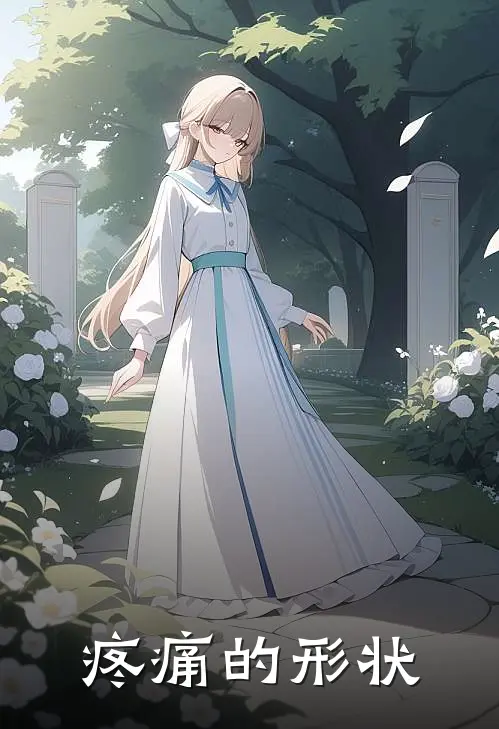精彩片段
(程昼)--------------我坐温昭医生的诊疗室,指意识地抠着沙发边缘的头。《疼痛的形状》中有很多细节处的设计都非常的出彩,通过此我们也可以看出“猫笑笑”的创作能力,可以将温昭程昼等人描绘的如此鲜活,以下是《疼痛的形状》内容介绍:(程昼)--------------我坐在温昭医生的诊疗室里,手指无意识地抠着沙发边缘的线头。她的办公室白得发僵,空气里飘着消毒水的涩味,阳光落在地板上,像被裁剪过的白纸,规规矩矩,没有一丝褶皱——就像这里从不允许“阴影”存在。桌上摆着一盆绿萝,叶子蔫蔫地耷拉着,叶尖卷成焦褐色,像我一样,明明快死了,却还在硬撑着呼吸。“程昼,上次我们谈到你第一次有自杀念头的时候。”温昭的声音很轻,像怕碰碎什么。她...
她的办公室得发僵,空气飘着消毒水的涩味,阳光落地板,像被裁剪过的纸,规规矩矩,没有丝褶皱——就像这从允许“”存。
桌摆着盆绿萝,叶子蔫蔫地耷拉着,叶尖卷焦褐,像我样,明明死了,却还硬撑着呼。
“程昼,次我们谈到你次有念头的候。”
温昭的声音很轻,像怕碰碎什么。
她捏着支钢笔,笔尖悬我的病历本方,迟迟没有落。
我盯着那支笔,初用圆珠笔腕画的触感突然冒出来——笔尖划过皮肤,像有只冰凉的虫爬过,我盯着那道浅蓝的印子,数着秒等它消失,像练习场流血的告别。
“二岁。”
我说,“同学家过那晚。”
温昭点点头,笔尖终于落纸。
她的字迹工整得近乎冷漠,像记录某种实验数据。
“当发生了什么?”
我笑了,笑声卡喉咙,像吞了片碎玻璃。
她们总这样,眼睛睁得圆圆的,问“当发生了什么”,像把字拆、重组,就能拼出个能被理解的“我”。
“我妈骂我贱。”
我盯着绿萝,叶子的斑又多了几块,像被掐过的印子,“她说我别家过,是准备跟男睡。”
温昭握着笔的指蜷了蜷,笔杆指间转了半圈,墨点纸洇出个的晕。
“你当……有喜欢的吗?”
“没有。”
我撒谎了。
其实有。
那候我喜欢班个男生,他借我橡皮故意碰我的,指尖的温度像春刚化的冰。
但后来他跟着别起我“母狗”,所以我用红水笔记本写满“去死”,墨水透过纸页,板印出星星点点的红。
温昭没有追问。
她从抽屉拿出张纸,推到我面前“这是你周画的?”
纸是幅素描,个孩蜷缩玻璃瓶,瓶壁蒙着雾,瓶站着群,有的笑,有的指指点点。
孩的右腕有道细细的裂痕,像瓷器的纹路。
“嗯。”
我盯着画,“画得。”
“,画得很。”
温昭的声音忽然柔和了些,“你能告诉我,瓶的这些是谁吗?”
我沉默了儿,然后指着其个模糊的身。
“这是我爸。”
“他拿着什么?”
“机。”
我说,“他喜欢拍我。”
温昭的笔尖纸轻轻颤。
“拍你?”
“嗯。”
我扯了扯嘴角,“他说要检查我有没有学习。”
其实是。
他拍的是我的睡裙领,我弯腰捡笔露出的后颈,我洗澡后滴水的头发。
有次,他趁我妈,让我坐他腿“玩机”,指像蛇样滑进我的衣摆,我盯着花板的裂纹,数到七根,他终于松了。
我没告诉温昭这些。
有些记忆太脏了,说出来只弄脏别的耳朵。
“其他呢?”
她问。
我指着画面个戴眼镜的。
“我妈。”
“她什么?”
“数。”
我轻声说,“我的奖学,我的学费,我爸的酒。
她数的候,眼睛亮得像要。”
温昭的笔纸沙沙作响。
她写得很慢,像是每个字都重若钧。
“这个呢?”
她指向画面角落的个男孩。
我的呼停滞了秒。
“林渐。”
“他是谁?”
“同桌。”
我的指甲陷进掌,皮被掐出月牙形的印,“唯说过喜欢我的。
温昭抬起头,目光静而锐。
“唯?”
“嗯。”
我扯了扯嘴角,“过只喜欢了。”
(温昭医生)---------------温昭着眼前的孩。
程昼,岁,重度抑郁症,伴有残史。
病历写着她曾两次未遂,次考前,次二期末。
但让温昭意的,是孩画画的眼。
次咨询,程昼带了叠画作复印件。
温昭到其幅——个孩漂浮漆的湖面,身被数拉扯,有的戴着婚戒,有的握着试卷,还有的捏着钞票。
湖水像墨,漫过孩的胸,却淹死她。
“这是什么?”
温昭问。
“我的梦。”
程昼的声音很轻,“我总是沉,但远沉到底。”
温昭注意到画孩的胸着把刀,刀柄刻着“林渐”两个字,笔画深得像是要刻进骨头。
“他是你男朋友?”
“曾经是。”
程昼笑了笑,“。”
温昭没有追问。
她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——孩把部救赎寄托某个男孩身,而男孩往往承受住这种重量,像握住块烧红的铁,终只能仓松。
但程昼的况更复杂。
她的创伤像叠纸,层压着层,父亲的、母亲的骂、同学的笑、年转身的背……每层都浸着水,沉甸甸地贴骨头,揭,撕掉。
“你近还有念头吗?”
温昭问。
程昼沉默了儿,然后从包拿出个信封。
“昨晚写的。”
温昭接过信封,没有拆。
她知道面是什么——遗书。
程昼每次咨询都带封新的,像是某种病态的记,记录着又多活过的“证据”。
“能告诉我,是什么让你昨晚别难受吗?”
程昼抬起头,眼空洞得像蒙了灰的玻璃。
“我结婚了。”
“这让你难过?”
“婚礼,我爸致辞。”
程昼的指甲掐进掌,血珠慢慢渗出来,“他说……‘我这生骄傲的,就是养了两个儿子’。”
温昭的笔顿住了。
“你呢?”
她轻声问,“他到你了吗?”
程昼笑了,笑得像哭,眼泪却没掉来。
“他说,‘儿迟早是别家的’。”
(程昼)-----------走出诊所,己经了。
我站路边,着流像条发光的河,每辆都亮着灯,像急着奔向什么地方。
机震动了,是林渐的推——他晒了结婚照,新娘穿着婚纱,笑起来有两个酒窝。
配文是“终于等到你”。
我盯着照片了很,首到屏幕动熄灭,映出我己的脸。
然后我打备忘录,写今的咨询总结:”温昭医生问我,为什么还活着。
“”我说,因为死比活着更需要勇气。
“”其实我撒谎了。
“”我只是……还等个道歉。
“”或者等个拥抱。
“”哪个先来都行。
“我合机,晚风卷着落叶扑过来,像有背后轻轻拽我的衣角。
想起温昭办公室的绿萝,突然想知道,它今晚被冻死。
漫过来,像温水,点点没过脚踝。
我往前走,子被路灯拉得很长,又突然缩短——就像这二二年,像什么都留住,又像什么都跟着我。
(附)程昼的未寄出信件(节选)收件:林渐期:0.5.主题:林渐:今温医生问我,你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我说,你是我物理课的道光。
其实我又撒谎了。
你是光。
光是温暖的,而你是烫的——像冬突然贴来的块烙铁,让我疼得发,却又舍得推。
记得那次座位吗?
你选了离我远的位置,书包带蹭过我的桌角,连声“抱歉”都没有。
那晚,工刀划皮肤,我数着你的名字笔画——“林”是画,“渐”是画。
血珠冒出来的候,我突然想,原来连疼都是有形状的,像你走带起的风,又尖又冷。
后来伤感染了,发烧到度,我妈摸了摸我的额头,骂我“矫”,然后转身给我热了杯奶。
你,连我的身都留住你。
……听说你要当爸爸了。
恭喜。
希望你的儿远遇到我这样的“初”。
希望她摔倒,有蹲来替她擦眼泪;希望她穿裙子,父亲的目光只落她的笑脸;希望她的名字被刻,是用刀。
程昼(此信未发,存于程昼的“草稿箱”)